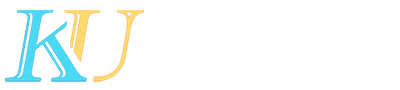內容目錄
當荷官是一種什麼體驗?

我在《南方人物周刊》實習期間,曾做過一篇有關荷官的職業報道。偶然發現這個問題,正好可以用作回答。總的來說,荷官在澳門是一個門檻不高的職業,只要你擁有了澳門本地居民身份(官方要求),就可以報名參加賭場提供的培訓。薪酬方面還算不錯,但是工作壓力也很大,澳門所有賭場都是24小時營業的,牌桌上的荷官們也像生產線的工人一樣,日夜輪換,流轉不停。文中講述的,是一個福建移民二代的職業故事。值得一提的是,當港陸矛盾正反復凸顯的時候,澳門大大小小的賭場里卻是人聲鼎沸,關閘碼頭車來人往,賭場內外笑臉相迎。個中緣由不言而喻。
澳門荷官的日與夜**
在賭桌後面正襟危坐的這5年,荷官陳鵬愈發明白:博彩是富人的游戲,而非窮人的賭局。僅僅在他工作過的上千個小時里,就足以窺見人們盲目的迷信、本性的自私和無盡的貪欲,在澳門島上一座座不分晝夜的金色宮殿內,隨著籌碼在桌面上的反復轉移而一再膨脹。
“我接受你的採訪,能得到什麼好處?”
他遞給我一根煙,被婉拒後夾在自己嘴裡點著,笑眯眯地看著我。這位每天至少手握兩千萬籌碼的賭場荷官,似乎需要一個能讓他滿意的答案。
上世紀70年代末,陳鵬父母從福建移民至澳門並成為永久居民,而他出生不久就被送回福建老家的爺爺奶奶身邊。高考後他放棄了上重點大學的機會,“回澳門基本上也是當荷官,沒學歷要求,還不如早點出來賺錢。”
2009年,19歲的陳鵬終於回到了他出生的島城,回歸到澳門本地人的社會身份。語言是首要障礙。在餐廳做了3個月兼職,他總算學會了些粵語。不久後他就到一家正在招聘的賭場報了名。
在澳門,博彩業已經成為公務員外社會評價最高的行業。最新發布的《澳門市民就業流動性調查(2014)報告》顯示,47.4%的跳槽者計劃轉行,娛樂博彩業成為首選。和陳鵬一同報名的五百多人里,不乏大學生和中年婦女。
陳鵬發現,比起高考,這種招聘考試只是小兒科。筆試要求兩分鐘內做20道運算題,他做對了18題。面試是做兩秒內口答的心算題,加減乘運算也難不倒他。接著是一個月的百家樂培訓,從學規則、記賠率到發牌、推籌碼,難度也越來越大。考試的要求是5分鐘內準確無誤地發10局牌,陳鵬一次過關。
陳鵬沒想到入行這麼順利:“幸好荷官只招本地人,在大陸找個月薪上萬的工作哪有這麼容易?”某位剛大學畢業的新同事也是一臉興奮:“我讀書時就在賭場做兼職,現在發現做全職工資比我的老師還高。”
賭場里負責賭桌一線工作的員工有4類:白襯衫黑馬甲的普通荷官在一樓大廳;紅色長袖外套的資深荷官在貴賓廳;每4張賭桌設一位監場主任;經理扮演著“救火隊員”的角色,處理各賭桌上的意外並作出決策。
上班第一天,看著十多位客人盯著自己,陳鵬心裡緊張得很,再加上耳邊不時的叫喊聲,發牌時手都在抖。派了一個小時的牌,他錯了兩次,都是沒算對籌碼。荷官出錯倒是常事,派牌派少了,籌碼賠多了,都要中止賭局,叫來經理,調看監控視頻後再處理。
算錯數,籌碼賠了出去也得收回。發錯牌,下註籌碼將被如數奉還。賭局作廢,荷官一般不會受罰,最不開心的是贏錢的賭客。陳鵬將一口煙徐徐吐出,突然加重了語氣:“不管怎樣,賭場是不可能給你錢的,甚至賠多了,只要你還在賭場,也會要回來,最多做個公關,免費給你住一晚豪華套房。”
荷官工作的學問也不少。籌碼疊數不同,擺法也不同,用手推出去時要夾在兩指間,食指呈90度彎曲狀,稱為“跪碼”。“以前的荷官贏了錢就用手敲兩下桌子,催促賭客拿錢出來。現在不同了,收籌碼都不能出聲,講究的是服務。”
“賭場不怕你贏錢,就怕你贏了錢就走。”巧合的堆積讓人相信規律的存在,每天緊盯著顯示結果的電腦屏幕找“路”的人不計其數。陳鵬也聽不懂“蟑螂路”、“小豬路”的說法:“根本沒有什麼路,如果說賭場有什麼風水,那就是站在科學這一邊。”
從兩三百到兩三萬的“咸魚翻身”,或是從百萬現金到空手而歸,類似的戲碼每天都在這座面積約為30平方公裡的島城重復上演。在陳鵬的印象里:輸光身家的賭徒抱著荷官大腿癱在地上痛哭;七八十歲的老太太到處兜售手上的玉鐲想要翻本;更有師奶在轉盤前信徒般雙手合十跪地祈禱;而某位大陸老闆輸掉5000萬面不改色,一周後又滿面春風地走進了貴賓廳。
還有一位留著小平頭的內地男子,在陳鵬面前把行李包拉鏈一扯,全是一沓沓港幣,一個人在百家樂賭桌上玩了起來。下註1萬塊贏了幾局之後,也許是感覺運氣來了,他一下子將10萬現金推出,待陳鵬為其換成籌碼後,直接擺在“閑”的格子上。結果開出的是“莊”。他扔出20萬港幣,再買“閑”,又是“莊”贏。“小平頭”鐵了心要把“閑”買中,賭註也從20萬、50萬加到100萬。

已經是一連12局的“莊”了。“小平頭”包里的現金所剩無幾,第13局他把150萬籌碼還押在“閑”上。圍觀者越來越多,陳鵬照常派牌、開牌,眾人伸長脖子一看,還是“莊”。“小平頭”一拳打在桌上,“怎麼搞的!”徑自走開。經理緊張地跑了過來,陳鵬故作輕松地說,“沒事沒事。”
“長莊哦,13局莊哦!”邊上的人議論了起來,隔壁賭桌一位客人聞訊而來,把50萬扔在“莊”上。陳鵬再次洗牌、發牌,開牌一看,是“閑”,一片嘩然。
“我見過的大陸客人素質都挺好,來貴賓廳玩的老闆們不在乎這十來萬。坦白講,我們不喜歡香港人,香港人真是“撲街”(混賬),賭得少,那些師奶去(最低下註)五百塊的桌子,只掏出兩三百塊搭在別人上面,輸了就指著鼻子問候你全家。”
陳鵬想起培訓官說的話,“你們沒看到大門口寫的是娛樂場嗎?我們公司不是賭場,是娛樂場!我們有酒店、有shopping mall,是供人娛樂的、開心的(地方)!”
陳鵬後來想明白了:在某種意義上,賭註下得越小的人,越緊張賭局的結果。“我們都習慣將上班的地方叫‘公司’,不是‘賭場’,香港人不是這樣想的,包括很多內地人也是,他們一過關就直奔賭場,輸了才走,他們是來賺錢的,不是來玩的。”
在澳門,賭場的數量在不斷刷新,和賭桌上翻滾的骰子一樣充滿變數。新賭場的開張意味著開啟了金錢與欲望不間歇流動的閘門,24小時營業直至其倒閉。超過25000名平均薪酬為17530澳門幣的荷官,在8小時制的輪值制度下維持著大約5750張賭桌的運轉。
陳鵬在入行3年後升為資深莊荷,如今月薪23000澳門幣。父母也因高薪酬在前些年轉行當荷官了,一家三口目前在同一家公司。其他賭場給荷官排的班有四五個,而陳鵬的公司多達9個,每周休息一天。他用手指著黑眼圈抱怨說:“有時要上兩個月的通宵更才能換班,真是沒人性。”
夜班上到早上五六點最難熬,很多荷官靠抽煙提神,陳鵬的煙癮也是這樣來的。入行不久他就體會到長夜難熬,某次休息間隙同事給他遞上一根煙,他一試:“還真行!”之後幾天沒抽,又困得不行,他趕緊去買了包萬寶路,直到現在一天一包,再也戒不掉。
陳鵬唯一的一次賭客經歷是在缺錢的時候。猶豫了兩天后,他才走進十六浦賭場,把錢包里的2000元全換成籌碼,坐在百家樂賭桌前。當荷官成為賭客,內心的不安和第一天上班的心情極其相似。3個小時下來,他贏了整整1萬塊。臨走時他決定再玩一局,下了1000塊,結果輸了,趕緊走人。
每天目睹著賭客們的人生起伏,陳鵬覺得自己的生活如同白開水。在澳門長大的堂哥也不像小時候那樣和他玩了,在街上打招呼也不應答,他感覺兩人已經不是同一類人了。“還是覺得和這里的人有很多不同,很開放,和他們玩不來,我以後也不會娶澳門女生。”陳鵬為數不多的好友都是福建移民子弟,偶爾約出去玩是他們最開心的事。
“其實人生也是賭來賭去啦,每一局的結果都會影響你下一次投註。”陳鵬自知是賭桌上保守的那一類人,他打算賺夠錢再出來做生意。父母移民給他的人生帶來了好運,他也想為下一代贏下更多的籌碼。(應受訪者要求,文中採訪對象為化名)
荷官,又稱莊荷,指賭場內負責發牌、處理籌碼的職業。由於荷官是在賭場里緊盯著客人的荷包(粵語,指錢包)的職員,且工作時保持嚴肅表情,故名“荷官”。
1澳門幣=0.78元人民幣(2014年12月匯率)